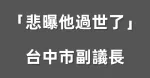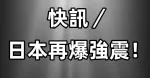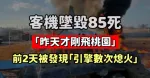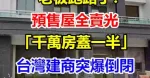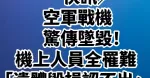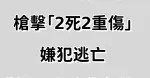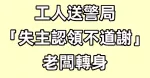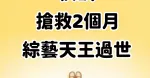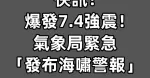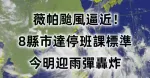3/3
下一頁
唐代著名的邊塞詩人,一生只寫6首詩,首首都是「王炸」,任憑一首都能獨步天下

3/3
有人不服:六首詩能叫詩人?唐代寫詩KPI考核怕是要給他打零分。同時代的張若虛靠《春江花月夜》封神,但好歹還寫了其他詩(雖然全丟了),王之渙這產量簡直像在文學史上「碰瓷」。更有人陰謀論:說不定是作品全弄丟了,只剩六首撿漏成爆款?歷史學者冷笑:同時代文人早把他的詩當教科書抄寫,同時期敦煌出土的文書里,《涼州詞》就有十七種抄本——唐代人用行動證明,這才是真頂流。
反轉來得猝不及防。2003年西安出土唐代墓志銘,赫然刻著王之渙擔任過「文安縣尉」——這個基層公務員居然在縣誌里被記載「每有詩作,頃刻傳誦」。同時期史料扒出更勁爆的:他那些「消失的詩」可能被戰火燒了,但當時文人聚會都以能背他的詩為榮。同時代大佬靳能在墓志銘里誇他「歌從軍,吟出塞,傳乎樂章,布在人口」,相當於現代被央視點名表揚。合著不是他寫得少,是歷史這個「硬碟」只給我們保留了六個文件?
但爭議沒完沒了。當代學者翻爛史料,確認他確實沒其他作品傳世。六首詩夠用嗎?
某些「文學評論家」還在掰扯數量決定論:六首詩也配和李白杜甫比?建議他們去翻翻《全唐詩》里那些量產詩人的作品——第兩百首和第一千首讀起來像複製粘貼。王之渙像是個在KTV只唱兩首歌的素人,結果一首拿下格萊美,一首衝上公告牌。那些嘲笑他「懶」的人,先想想自己能不能用六條微博火遍千年?當杜甫為「語不驚人死不休」撓禿頭時,王之渙早用「更上一層樓」給所有詩人上了一課:精品率才是王道。
語文課本該不該給王之渙開VIP通道?李白杜甫寫一千首才混到三四篇課文,他六首就占兩席,這是教育界的「倖存者偏差」還是赤裸裸的偏心眼?支持者說好詩一句頂萬句,反對者罵這是鼓勵「躺平文學」——要是詩人都學他六年寫六句,唐詩三百首得改名叫《唐詩三十首》了。你怎麼看?
反轉來得猝不及防。2003年西安出土唐代墓志銘,赫然刻著王之渙擔任過「文安縣尉」——這個基層公務員居然在縣誌里被記載「每有詩作,頃刻傳誦」。同時期史料扒出更勁爆的:他那些「消失的詩」可能被戰火燒了,但當時文人聚會都以能背他的詩為榮。同時代大佬靳能在墓志銘里誇他「歌從軍,吟出塞,傳乎樂章,布在人口」,相當於現代被央視點名表揚。合著不是他寫得少,是歷史這個「硬碟」只給我們保留了六個文件?
但爭議沒完沒了。當代學者翻爛史料,確認他確實沒其他作品傳世。六首詩夠用嗎?
某些「文學評論家」還在掰扯數量決定論:六首詩也配和李白杜甫比?建議他們去翻翻《全唐詩》里那些量產詩人的作品——第兩百首和第一千首讀起來像複製粘貼。王之渙像是個在KTV只唱兩首歌的素人,結果一首拿下格萊美,一首衝上公告牌。那些嘲笑他「懶」的人,先想想自己能不能用六條微博火遍千年?當杜甫為「語不驚人死不休」撓禿頭時,王之渙早用「更上一層樓」給所有詩人上了一課:精品率才是王道。
語文課本該不該給王之渙開VIP通道?李白杜甫寫一千首才混到三四篇課文,他六首就占兩席,這是教育界的「倖存者偏差」還是赤裸裸的偏心眼?支持者說好詩一句頂萬句,反對者罵這是鼓勵「躺平文學」——要是詩人都學他六年寫六句,唐詩三百首得改名叫《唐詩三十首》了。你怎麼看?
 呂純弘 • 193K次觀看
呂純弘 • 193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65K次觀看
呂純弘 • 65K次觀看 舒黛葉 • 4K次觀看
舒黛葉 • 4K次觀看 舒黛葉 • 16K次觀看
舒黛葉 • 16K次觀看 舒黛葉 • 7K次觀看
舒黛葉 • 7K次觀看 呂純弘 • 9K次觀看
呂純弘 • 9K次觀看 花峰婉 • 8K次觀看
花峰婉 • 8K次觀看 舒黛葉 • 20K次觀看
舒黛葉 • 20K次觀看 呂純弘 • 9K次觀看
呂純弘 • 9K次觀看 呂純弘 • 18K次觀看
呂純弘 • 18K次觀看 管輝若 • 8K次觀看
管輝若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14K次觀看
呂純弘 • 14K次觀看 呂純弘 • 9K次觀看
呂純弘 • 9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舒黛葉 • 40K次觀看
舒黛葉 • 40K次觀看 管輝若 • 7K次觀看
管輝若 • 7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14K次觀看
呂純弘 • 14K次觀看 舒黛葉 • 6K次觀看
舒黛葉 • 6K次觀看 舒黛葉 • 12K次觀看
舒黛葉 • 12K次觀看 呂純弘 • 20K次觀看
呂純弘 • 20K次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