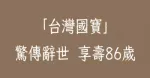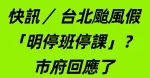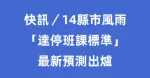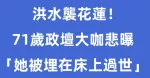3/3
下一頁
紀曉嵐嫁女,陪嫁一個破碗,被恥笑十年女婿想摔碗,看到碗底傻眼

3/3
「啪」的一聲脆響,把孩子打懵了,也把一旁的紀筠打傻了。
孩子「哇」地一聲哭出來。祝汝昌看著兒子臉上的紅印,自己也愣住了。他踉蹌著退後幾步,蹲在牆角,像個孩子一樣抱頭痛哭起來。
那一晚,家裡是十年未有的死寂。
第二件,是祝汝昌一位昔日同窗的到訪。此人姓王,當年曾與祝汝昌一同進京趕考,落榜後走了門路,捐了個官,如今已是江南某縣的縣令。這次因公入京,特意前來「看望」祝汝昌。
那王縣令一身嶄新的官服,氣度不凡,被下人引著走進這破敗的小院時,眉宇間閃過一絲毫不掩飾的鄙夷。他與祝汝昌寒暄,言語間滿是炫耀自己的政績和前程,又時不時地對祝汝昌的處境表示「惋惜」和「同情」。
臨走時,他從袖子裡摸出一錠足有十兩的雪花銀,不由分說地塞到祝汝昌手裡,拍著他的肩膀,語重心長地說:「汝昌兄,你我同窗一場,這點心意務必收下。讀書……有時候也要看命啊。你守著嫂夫人和孩子,不容易。」
那副高高在上的施捨嘴臉,徹底擊垮了祝汝昌的最後一道心理防線。
等王縣令前腳剛邁出院門,祝汝昌便追了出去,將那錠銀子狠狠地砸在了他腳下的青石板上,發出「鐺」的一聲巨響。
「我祝汝昌還沒死!用不著你來可憐!」他嘶吼道。
王縣令回過頭,也不生氣,只是輕蔑地冷笑一聲,撣了撣衣袍上並不存在的灰塵,搖著頭,坐上轎子,揚長而去。
祝汝昌呆呆地站在門口,看著那錠在地上閃著刺眼光芒的銀子,感覺自己整個世界,都崩塌了。
04
壓垮駱駝的,從來不是最後一根稻草,而是它身上背負的每一根。而對於祝汝昌來說,那根最沉重的稻草,終於還是落了下來。
院子的房東來了。一個腦滿腸肥的市儈商人,捏著兩撇鼠須,斜著眼睛通知祝汝昌,從下個月起,房租要漲一倍。
「祝先生,不是我老張不講情面。您在我這兒住了快十年了,這房租就沒漲過。可您瞧瞧,如今京城的物價,哪樣不漲?我這也是小本買賣,實在是……扛不住了。」房東說得一臉為難,眼神里卻滿是精明和不耐。
祝汝昌知道他是在撒謊。周圍的房價根本沒漲,這分明是看他們家窮,想把他們趕走。他壓著火氣,低聲下氣地與房東理論、商量,希望能寬限幾天,或者少漲一些。
房東卻徹底撕破了臉皮,指著祝汝昌的鼻子,刻薄地說道:「祝汝昌!我也不跟你繞彎子了!你住進來的時候是個窮秀才,十年過去了,你還是個窮秀才!人人都說我這院子風水好,可別都被你這十年不變的晦氣給衝撞了!一句話,下個月,要麼交雙倍的房租,要麼捲舖蓋走人!」
這番話,如同一記響亮的耳光,狠狠地扇在了祝汝昌的臉上。他失魂落魄地回到家,整個人都像是被抽走了魂魄。
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這節骨眼上,他們的小女兒也病倒了,咳嗽不止,小臉蠟黃,看著就讓人心疼。紀筠翻箱倒櫃,把家裡最後幾件能換錢的破爛,甚至自己頭上那根用了多年的舊銀簪都找了出來,在心裡盤算了一遍又一遍,全部家當加起來,連下個月一半的房租都付不起,更別提給女兒請大夫抓藥了。
夜深了,孩子們在裡屋睡著,女兒的咳嗽聲一陣陣傳來,像小錘子一樣,敲在夫妻倆的心上。
紀筠看著祝汝昌那張毫無生氣的、絕望的臉,終於下定了決心。她走到丈夫面前,跪了下來,淚水像斷了線的珠子,滾滾而下。
「夫君,算我求你了……我們……我們回娘家吧。」她的聲音都在發抖,「哪怕只是回去暫住一陣子,先給孩子看病,再圖將來。低一次頭,就低一次頭,不丟人!為了孩子,行嗎?」
「回娘家」這三個字,像一道天雷,轟然劈中了祝汝昌。這三個字又像一根點燃了的火信,瞬間引爆了他胸中積壓了整整十年的所有怨氣、屈辱、不甘和憤怒!
他猛地從椅子上站了起來,雙眼赤紅,面目猙獰,像一頭被逼入絕境的野獸。
「不——行!」他從牙縫裡擠出這兩個字。
他的腦子裡一片混亂,無數個畫面在飛速閃現。新婚之夜那隻刺眼的破碗,街坊鄰居的指指點點,茶館書生的戲謔,當鋪朝奉的輕蔑,昔日同窗的施捨,房東刻薄的嘴臉……十年!整整十年啊!
他祝汝昌,曾經也是鄉里寄予厚望的才子,曾經也對未來充滿了無限的嚮往!可如今呢?他成了一個人人可以踩上一腳的廢物,一個連妻兒都無法庇護的懦夫,一個全京城最大的笑話!
他的人生,就像這隻破碗,充滿了無法彌補的缺憾和裂痕!
他恨!恨紀曉嵐那個高高在上的老東西,躲在雲端之上,冷眼旁觀,看了他十年的笑話,想必心裡一定很得意吧!恨這個拜高踩低、世態炎涼的世界!更恨自己這身沒用的骨頭,怎麼就這麼不爭氣!
這一切的源頭是什麼?
就是那隻碗!那隻該死的破碗!是它,像一個詛咒,籠罩了他整整十年!是它,讓他背負了十年的枷鎖和恥辱!
對!就是它!
祝汝昌像是突然找到了所有痛苦的宣洩口,他跌跌撞撞地衝到屋角那個放碗的木架前,一把將那隻蒙著薄塵的破碗狠狠地抓在手裡。
這些年,他有過無數次想把它砸碎的衝動,但每一次,要麼被紀筠聲淚俱下地攔住,要麼就是被那句「不到山窮水盡」的鬼話所束縛。
今天,他覺得,自己已經死了。精神上,徹徹底底地死了。還有什麼,比現在更山窮水盡的?還有什麼,比眼睜睜看著女兒病重、全家即將流落街頭更絕望的?
沒有了!
他高高地舉起那隻碗,對著嚇得面無人色的紀筠,發出了狀若瘋狂的大笑,笑聲里充滿了悽厲和絕望。
「十年了!紀筠!你看到了嗎?整整十年了!我祝汝昌就是個天大的笑話!你爹送的這個『寶貝』,這個破碗,就是我祝汝昌的命!今天,我就親手把這條爛命給砸了!」
「什麼狗屁深意!什麼狗屁考驗!全都是騙人的!騙人的!!我再也不信了!!」
他歇斯底里地咆哮著,用盡全身的力氣,將碗高高地舉過了頭頂,手臂上的青筋虯結暴起,對準了腳下那片堅硬冰冷的青石板,狠狠地——砸了下去!
05
「不要——!」
紀筠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尖叫,她不顧一切地撲了過來,想要阻止丈夫這個瘋狂的舉動。裡屋的孩子們也被這恐怖的咆哮和母親的哭喊聲驚醒,發出了驚懼的大哭。
整個狹小而破敗的屋子裡,瞬間被絕望的氣息填滿。空氣仿佛凝固了,時間也似乎在這一刻被無限放慢。
祝汝昌的眼中,只剩下那片即將與碗碰撞的青石地面。他要砸碎它!砸碎這個折磨了他十年的噩夢!砸碎他這屈辱不堪的命運!
他的手腕已經開始發力,那隻破碗帶著風聲,以決絕的姿態向著地面墜落。
然而,就在他的手腕即將發力到極致、碗即將脫手而出的那一剎那,或許是由於情緒激動而手心出汗,又或許是剛才抓握得太過用力,他的大拇指,在碗底那個粗糙的、沒有上釉的圈足上,重重地、狠狠地滑了一下。
突然之間,祝汝他所有的動作,都僵在了那零點零一秒。那股毀天滅地般的滔天怒火,那份與世界同歸於盡的瘋狂決絕,仿佛被指尖傳來的一絲微不可察的異樣觸感,瞬間澆上了一盆冰水。
他的指尖,傳來一種極其奇怪的感覺。
不是普通陶土燒制後留下的那種粗糲、砂礫般的質感。而是在那一片粗糲之中,有一道極其細微、卻又異常清晰的凸起劃痕。它很短,很淺,若不刻意去摸,根本無法察覺。
但它又不同於燒窯時偶然留下的瑕疵,因為祝汝昌能清晰地感覺到,這道凸起有規律,有稜角,甚至……有筆鋒。
它像是……被人為刻上去的!
祝汝昌愣住了,像一尊石化的雕像,依舊保持著那個將碗砸向地面的姿勢,一動不動。他的大腦一片空白,所有的聲音——妻子的哀求,孩子的哭喊,窗外的風聲——全都在瞬間離他遠去。
這是什麼?
這個念頭像一顆石子,投進了他死寂的心湖。
十年了。整整十年,這隻碗就擺在他的家裡。他看過它無數次,也曾在盛怒之下摸過它幾次。可他從來沒有,也從來不屑於去仔細地觀察它的碗底。在他眼裡,這就是一件象徵著恥辱的垃圾。
偏偏在今天,在他最絕望、最痛苦、最瘋狂的時刻,在他下定決心要將它徹底毀滅的這一刻,這個隱藏了十年的秘密,才吝嗇地、悄悄地,向他展露了冰山一角。
這算什麼?是命運的又一次捉弄嗎?
祝汝昌慢慢地,幾乎是帶著一種神經質的顫抖,將高舉的胳T膊緩緩放了下來。
紀筠的哭聲戛然而止,她滿臉淚痕,不解地看著丈夫這奇怪的舉動。她以為他回心轉意了,連忙上前,想要去拿他手中的碗。
「別碰!」
祝汝昌低喝一聲,像是護著什麼稀世珍寶一樣,將碗緊緊地抱在了懷裡。
他沒有理會任何人,徑直走到那張破舊的方桌前,借著窗外滲透進來的、微弱的清冷月光,小心翼翼地將碗翻了過來,讓碗底朝上。
他低下頭,將眼睛湊了上去,近得幾乎要貼在碗底。
他屏住呼吸,伸出微微顫抖的食指,在那道神秘的、被污垢和歲月掩蓋的凸起上,反覆地、輕輕地摩挲著。
他的呼吸,一點一點地,變得急促起來。
那不是一道簡單的劃痕。
那是一個字。
一個用某種極其古老、他從未見過的篆體刻下的、小到幾乎無法用肉眼辨認的字……
06
祝汝昌像是著了魔。
他小心翼翼地捧著那隻碗,仿佛捧著的是一個剛剛降生的嬰兒。他讓紀筠打來一盆清水,然後親手、仔仔細細地,將那隻碗里里外外清洗了無數遍。他洗得極其認真,連碗口那處豁口的陳年茶漬都不放過,尤其是碗底的圈足,他用一塊軟布,蘸著水,一寸一寸地擦拭,生怕錯漏了任何細節。
紀筠站在一旁,看著丈夫這判若兩人的舉動,心中充滿了疑惑和一絲隱隱的期待。她看到丈夫的眼神,那是一種她已經有十年沒有見過的眼神——專注、探究、閃爍著一個讀書人獨有的、智慧的光芒。
當碗底圈足上最後一絲污垢被清水洗去,那個神秘的字,終於在微弱的油燈光下,顯露出了它的廬山真面目。
它非常小,刻工卻異常精湛。筆畫轉折之間,遒勁有力,充滿了古樸之意。
祝汝昌可以肯定,這絕不是一個常見的漢字。他飽讀詩書,經史子集無一不通,卻從未在任何典籍上見過這個字形。它更像是一種特殊的符號,一個專屬的印記。
一個「款」。
祝汝昌的腦中瞬間閃過這個詞。古代的瓷器,尤其是珍貴的官窯或私家窯口燒制的精品,往往會在器物底部留下特殊的款識,以作標記。
「筠兒,快,把我書箱裡那幾本講古玩雜項的書都拿來!」祝汝昌的聲音裡帶著一絲壓抑不住的激動。
紀筠立刻回過神來,手忙腳亂地把他那幾口破舊的書箱打開,將裡面那些紙頁泛黃、甚至有些殘破的藏書都抱了出來。
夫妻二人就在這盞昏黃的油燈下,把頭湊在一起,開始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探尋。祝汝昌一頁一頁地翻著書,紀筠則在一旁,舉著油燈,為他照亮。十年來的隔閡與冷漠,仿佛在這一刻悄然消融,他們又變回了當初那對心意相通、互相扶持的伴侶。
他們翻遍了《陶說》、《景德鎮陶錄》這些常見的書籍,一無所獲。祝汝昌並不氣餒,又從箱底翻出幾本市面上極為罕見的孤本殘卷。這些書,還是他當年進京時,從一個落魄老秀才手裡淘來的寶貝。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窗外的天色已經開始泛白。就在紀筠的眼皮開始打架,祝汝昌也快要放棄的時候,他的手指在一頁殘破的紙上停住了。
那是一本名為《古窯考》的殘卷,上面用蠅頭小楷記錄了許多早已湮沒在歷史長河中的古代窯口和款識。
祝汝昌的目光,死死地鎖定在了其中一段記載上。書上畫著一個與碗底那個字一模一樣的符號!
他的心「砰砰」地狂跳起來。
他指著那個字,聲音因為激動而微微發顫:「筠兒,你……你看!是它!就是它!」
紀筠也湊了過來,只見書上赫然寫著:
「前朝寧王,性好奢,於封地建私窯,延攬天下名匠,專燒秘瓷。其泥料甚奇,摻西域『流光石』粉末,燒成之器,迎光細察,可見五彩毫光流轉,肉眼幾不可辨,世稱『流光瓷』。瓷成,皆於器底足內,以精鋼之錐,刻『押』字暗款,其形如……」
後面的字跡已經模糊不清,但「押」字暗款這四個字,如同一道閃電,劈開了祝汝昌腦中的所有迷霧!
這個字,竟然是一個「押」!它不是產地,也不是工匠名,而是前朝一位權勢滔天的藩王——寧王府私家窯口的憑證!
祝汝昌立刻將碗舉起,對著從窗戶縫隙透進來的第一縷晨光,眯起眼睛仔細觀察。果然,他看到碗壁內側,隨著光線的轉動,有一層幾乎看不見的、如同彩虹般的淡淡光暈在緩緩流動!
若非事先知道,誰能發現這隻粗陋破碗上,竟藏著如此玄機!
可這又如何呢?即便這是價值連城的「流光瓷」,一隻破了口的碗,又能值幾個錢?難道紀曉嵐讓他等十年,就是為了讓他發現這是個古董?
祝汝昌的眉頭又皺了起來,他覺得事情沒那麼簡單。他強迫自己冷靜下來,繼續往下看那段殘存的文字。
在「押」字款的圖樣下面,還有一行模糊的小字,像是後人加上的註解:
「……寧王事敗,家財散盡,其後人輾轉流落。聞寧王曾於京中設一錢莊為退路,後易名為『德昌記』當鋪,世代相傳。凡持『押』字款信物者,皆可至此……」
後面的文字,被蟲蛀掉了一個大洞。
但「德昌記」當鋪這四個字,清晰無比!
祝汝昌和紀筠對視一眼,都在對方的眼中看到了震驚和不敢置信。
德昌記當鋪!那不是就在他們家往東兩條街外,那家門面小得毫不起眼,看起來總是半死不活的當鋪嗎?祝汝昌曾無數次路過那裡,甚至有幾次窘迫到了極點,想進去當掉身上最後一件值錢的東西,但都因為那家店看起來生意太冷清,怕當不了幾個錢而作罷。
一個瘋狂的念頭,在祝汝昌的腦海中形成。
這隻碗,不僅僅是一隻碗。
它是一把鑰匙!一把開啟某個巨大秘密的鑰匙!
07
天一亮,祝汝昌就再也坐不住了。
他將那隻碗用布里三層外三層地包好,小心翼翼地揣進懷裡,那神情,比當年赴京趕考時揣著自己的得意文章還要鄭重。
「夫君,我跟你一起去。」紀筠不放心,堅持要陪著他。
祝汝昌看著妻子擔憂的眼神,點了點頭。他牽起紀筠的手,十年了,他第一次如此用力地、堅定地握著她的手。
夫妻二人懷著一種近乎朝聖般的忐忑心情,來到了那家「德昌記」當鋪門前。
這家當鋪的門面確實太小了,夾在兩家熱鬧的雜貨鋪中間,不仔細看根本發現不了。一塊褪了色的「德昌記」牌匾歪歪斜斜地掛著,門前的櫃檯積了一層薄灰,櫃檯後面,一個頭髮花白、看起來隨時都能睡過去的老頭,正有一下沒一下地打著算盤。
看到祝汝昌和紀筠進來,那老師傅連眼皮都沒抬一下,懶洋洋地問:「當東西?」
祝汝昌深吸一口氣,走上前,並沒有拿出懷裡的碗,而是壓低聲音,試探性地問:「老師傅,晚生想請教一下,您這裡……可認得一種『押』字款的信物?」
他話音剛落,那原本昏昏欲睡的老師傅,渾身猛地一震。他那雙渾濁的老眼瞬間睜開,射出一道精光,上上下下地將祝汝昌打量了一遍,又看了看他身邊的紀筠。
「東西帶來了嗎?」老師傅的聲音變得沉穩而嚴肅。
祝汝昌心中一凜,知道自己找對地方了。他從懷中,小心翼翼地取出那只用布包著的破碗,放在了櫃檯上,然後將碗底翻了過來,露出了那個清晰的「押」字。
老師傅的眼睛瞬間亮了。他戴上一副老花鏡,從抽屜里取出一個類似放大鏡的奇特工具,對著那個「押」字,仔仔細細地勘驗了半晌。他又用指甲在碗壁上輕輕颳了一下,湊到光線下反覆察看。
半晌,他放下工具,長長地舒了一口氣,臉上露出了如釋重負的表情。
他對著祝汝昌和紀筠,恭恭敬敬地躬身一揖:「二位貴客,小老兒……等了你們十年了!」
說完,他不再多言,繞出櫃檯,將二人請進了當鋪的內堂。
內堂陳設簡單,卻打掃得一塵不染。老師傅關上門,從牆角一個不起眼的暗格里,吃力地拖出一個巨大的、上了銅鎖的樟木箱子。
「祝相公,紀小姐,」老師傅擦了擦額頭的汗,語氣里充滿了敬意,「十年前,紀大學士親自來到這裡,存下了這個箱子,並留下了這隻碗作為信物。大人當時交代,這箱子裡的東西,是給二姑爺和二小姐的。但是,有一個規矩。」
祝汝昌屏息凝神地聽著。
「大人說,只有當他的女婿,祝相公您,親自、並且是獨立地發現了這碗底的秘密,悟到了其中的玄機,才能來取。若是紀小姐您,或者紀府的其他人拿著這隻碗來,小老兒一概不認。」
「大人還說,」老師傅看了一眼祝汝昌,眼神複雜,「若是這隻碗,在中途被打碎了,那麼這個箱子,將由小老兒親手焚毀,永遠封存。」
祝汝昌聽到這裡,只覺得背後一陣冷汗。他想起了昨夜,那隻碗離地面只有咫尺之遙,只要他再多用一分力,只要他的手指沒有那一下鬼使神差的滑動,這箱子裡的一切,就將與他永遠失之交臂。
老師傅用一把古舊的鑰匙,打開了銅鎖,「咔噠」一聲,在寂靜的內堂里顯得格外清脆。
他掀開了沉重的箱蓋。
箱子裡面,沒有祝汝昌想像中的金銀珠寶,黃白之物。
最上面一層,是厚厚的一疊地契和房契。祝汝昌顫抖著手拿起來一看,上面赫然寫著:京郊良田三百畝,城中臨街旺鋪三間!
這……這才是真正的嫁妝!
紀筠也捂住了嘴,眼中滿是淚水。
祝汝昌接著往下看,箱子的中層,整整齊齊地碼放著數百冊書籍。他只抽出一本來看,便呼吸一滯。那是一本宋版的《資治通鑑》殘卷,是市面上早已絕版的孤本!他再翻看其他的書,無一不是價值連城的古籍善本。對於一個真正的讀書人來說,這比金山銀山還要寶貴!
而在箱子的最底層,靜靜地躺著一張摺疊的素箋。它沒有用信封封口,更像是一張隨手寫下的留言條。
祝汝昌拿起那張素箋,展開。
上面,是紀曉嵐那熟悉而蒼勁的筆跡,只有短短兩行字:
器毀則才亡,人窮則志堅。
十年磨一劍,今朝始出鞘。
短短十六個字,像十六記重錘,狠狠地敲在了祝汝昌的心上。
在這一瞬間,所有的屈辱,所有的不甘,所有的怨恨,都化為了醍醐灌頂般的徹骨明悟!
他終於明白了!他全明白了!
岳父紀曉嵐,根本不是在羞辱他,也不是在看他的笑話。他是在用一種最極端、最殘酷的方式,磨練他的心性!
如果十年前,岳父直接把這些財富交給他,以他當時年少得志、心高氣傲的心態,極有可能會被這突如其來的富貴迷了心竅,從此耽於享樂,荒廢了學業和銳氣。
所以,岳父給了他一隻破碗,給了他一個「破碗女婿」的惡名,讓他從雲端跌入泥淖,讓他嘗盡人間冷暖、世態炎涼。他要磨掉他身上的浮躁之氣,要鍛鍊他處變不驚的韌性,要看看他在這真正的「山窮水盡」之中,是否還能保持一個讀書人的風骨、一個逆境求生者的觀察力,去發現那個近在眼前、卻又被所有人忽視的秘密!
「器毀則才亡」,如果他連這點挫折都承受不住,心灰意冷,甚至遷怒於物,將碗砸碎,那就證明他心智脆弱,不堪大用,才華也終將因此而毀滅。
「人窮則志堅」,只有經歷過真正的貧窮和絕望,才能真正懂得民生疾苦,才能磨練出堅不可摧的意志。
這隻破碗,既是十年殘酷的考驗,也是一道最嚴密的保護。它保護了他的初心,砥礪了他的心志。這十年的白眼,十年的屈辱,這十年所有的苦難,原來,才是岳父贈予他的一生中最寶貴、最厚重的一筆財富!
祝汝昌手捧著那些地契和書冊,看著那兩行字,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他這個七尺男兒,「噗通」一聲跪倒在地,朝著紀府的方向,泣不成聲,重重地、一個接一個地,磕了三個響頭。
這一拜,是悔恨。
這一拜,是感激。
這一拜,是新生。
08
有了田產和商鋪的穩定收入,祝汝昌一家的生活,幾乎是一夜之間,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那些田地和鋪子,早就由紀府的忠僕代為打理得井井有條,每年都有極為可觀的進項。
他再也不需要為了下一頓飯而發愁,再也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臉色。
但他沒有像那些一夜暴富的庸人一樣,立刻搬進豪宅,買奴僕,穿錦衣。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揣著銀子,去城裡最好的藥鋪,為女兒請了最好的大夫,抓了最好的藥。看著女兒的病一天天好起來,重新恢復了活潑,他覺得比自己中了狀元還要高興。
第二件事,他用一筆錢,把他住了十年的那間破敗小院給買了下來。紀筠不解,問他為何不換個大宅子。祝汝昌只是笑了笑,說:「這裡,是我們真正的家。我不想忘了我們是從哪裡走出來的。」
他把院子重新修葺了一番,尤其那間小小的書房,他換上了寬大的書案和明亮的窗戶,然後將那幾百冊從「德昌記」取回的孤本古籍,一本本地、視若珍寶地擺上了新做的書架。
整個人,從裡到外,都變了。
他不再是那個敏感自卑、眼神麻木的中年人,也不再是那個憤世嫉俗、動輒發怒的酒鬼。他腰杆重新挺直了,眼神也重新變得清亮、沉穩、溫和。那十年歲月刻下的風霜,仿佛一夜之間被撫平,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經歷過大起大落後的淡定與從容。
他待人接物,平和謙遜。那些曾經嘲笑過他、鄙夷過他的街坊鄰里,見到他如今的變化和富裕,一個個都換上了恭敬諂媚的笑臉,變著法兒地來巴結討好。祝汝昌並不在意,也從不報復,只是淡淡一笑,與他們保持著不遠不近的距離。
心無旁騖之後,祝汝昌將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學問之中。他白日裡研讀那些珍貴的古籍,夜晚則靜坐思考。十年的底層生活,讓他對民生疾苦有了最深刻的洞察。他的文章,褪去了年少時的華而不實,變得老辣而深刻,字裡行間充滿了對現實的關懷和悲憫。
又過了三年,朝廷再開恩科。祝汝昌平靜地走進了曾經讓他三次折戟的貢院。
這一次,他下筆從容,一氣呵成。放榜之日,他的名字赫然在列,高中二甲進士。雖然不是狀元,但這個成績,足以讓他踏入仕途,實現自己真正的抱負。主考官在批閱他的策論時,曾大加讚賞,稱其「言之有物,字字泣血,非經歷世事者不能為此文」。
故事的結尾,是幾年後的一個冬日。紀曉嵐七十大壽,紀府高朋滿座,熱鬧非凡。
祝汝昌身著一身得體的官服,氣度不凡,早已不是當年那個窘迫的寒門書生。他牽著溫婉賢淑的紀筠,帶著一雙活潑可愛的兒女,回到了紀府,為岳父祝壽。
席間,他沒有提當年任何事,也沒有說任何感激的話。只是在壽宴開始前,親手為岳父紀曉嵐奉上了一杯新茶。
紀曉嵐端坐在太師椅上,看著眼前這個氣度沉穩、眼神堅毅的女婿,接過茶杯,輕輕抿了一口。他渾濁而睿智的眼中,閃過一絲滿意的笑意,捋著花白的鬍鬚,點了點頭。
翁婿二人相視一笑,一切盡在不言中。
孩子「哇」地一聲哭出來。祝汝昌看著兒子臉上的紅印,自己也愣住了。他踉蹌著退後幾步,蹲在牆角,像個孩子一樣抱頭痛哭起來。
那一晚,家裡是十年未有的死寂。
第二件,是祝汝昌一位昔日同窗的到訪。此人姓王,當年曾與祝汝昌一同進京趕考,落榜後走了門路,捐了個官,如今已是江南某縣的縣令。這次因公入京,特意前來「看望」祝汝昌。
那王縣令一身嶄新的官服,氣度不凡,被下人引著走進這破敗的小院時,眉宇間閃過一絲毫不掩飾的鄙夷。他與祝汝昌寒暄,言語間滿是炫耀自己的政績和前程,又時不時地對祝汝昌的處境表示「惋惜」和「同情」。
臨走時,他從袖子裡摸出一錠足有十兩的雪花銀,不由分說地塞到祝汝昌手裡,拍著他的肩膀,語重心長地說:「汝昌兄,你我同窗一場,這點心意務必收下。讀書……有時候也要看命啊。你守著嫂夫人和孩子,不容易。」
那副高高在上的施捨嘴臉,徹底擊垮了祝汝昌的最後一道心理防線。
等王縣令前腳剛邁出院門,祝汝昌便追了出去,將那錠銀子狠狠地砸在了他腳下的青石板上,發出「鐺」的一聲巨響。
「我祝汝昌還沒死!用不著你來可憐!」他嘶吼道。
王縣令回過頭,也不生氣,只是輕蔑地冷笑一聲,撣了撣衣袍上並不存在的灰塵,搖著頭,坐上轎子,揚長而去。
祝汝昌呆呆地站在門口,看著那錠在地上閃著刺眼光芒的銀子,感覺自己整個世界,都崩塌了。
04
壓垮駱駝的,從來不是最後一根稻草,而是它身上背負的每一根。而對於祝汝昌來說,那根最沉重的稻草,終於還是落了下來。
院子的房東來了。一個腦滿腸肥的市儈商人,捏著兩撇鼠須,斜著眼睛通知祝汝昌,從下個月起,房租要漲一倍。
「祝先生,不是我老張不講情面。您在我這兒住了快十年了,這房租就沒漲過。可您瞧瞧,如今京城的物價,哪樣不漲?我這也是小本買賣,實在是……扛不住了。」房東說得一臉為難,眼神里卻滿是精明和不耐。
祝汝昌知道他是在撒謊。周圍的房價根本沒漲,這分明是看他們家窮,想把他們趕走。他壓著火氣,低聲下氣地與房東理論、商量,希望能寬限幾天,或者少漲一些。
房東卻徹底撕破了臉皮,指著祝汝昌的鼻子,刻薄地說道:「祝汝昌!我也不跟你繞彎子了!你住進來的時候是個窮秀才,十年過去了,你還是個窮秀才!人人都說我這院子風水好,可別都被你這十年不變的晦氣給衝撞了!一句話,下個月,要麼交雙倍的房租,要麼捲舖蓋走人!」
這番話,如同一記響亮的耳光,狠狠地扇在了祝汝昌的臉上。他失魂落魄地回到家,整個人都像是被抽走了魂魄。
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這節骨眼上,他們的小女兒也病倒了,咳嗽不止,小臉蠟黃,看著就讓人心疼。紀筠翻箱倒櫃,把家裡最後幾件能換錢的破爛,甚至自己頭上那根用了多年的舊銀簪都找了出來,在心裡盤算了一遍又一遍,全部家當加起來,連下個月一半的房租都付不起,更別提給女兒請大夫抓藥了。
夜深了,孩子們在裡屋睡著,女兒的咳嗽聲一陣陣傳來,像小錘子一樣,敲在夫妻倆的心上。
紀筠看著祝汝昌那張毫無生氣的、絕望的臉,終於下定了決心。她走到丈夫面前,跪了下來,淚水像斷了線的珠子,滾滾而下。
「夫君,算我求你了……我們……我們回娘家吧。」她的聲音都在發抖,「哪怕只是回去暫住一陣子,先給孩子看病,再圖將來。低一次頭,就低一次頭,不丟人!為了孩子,行嗎?」
「回娘家」這三個字,像一道天雷,轟然劈中了祝汝昌。這三個字又像一根點燃了的火信,瞬間引爆了他胸中積壓了整整十年的所有怨氣、屈辱、不甘和憤怒!
他猛地從椅子上站了起來,雙眼赤紅,面目猙獰,像一頭被逼入絕境的野獸。
「不——行!」他從牙縫裡擠出這兩個字。
他的腦子裡一片混亂,無數個畫面在飛速閃現。新婚之夜那隻刺眼的破碗,街坊鄰居的指指點點,茶館書生的戲謔,當鋪朝奉的輕蔑,昔日同窗的施捨,房東刻薄的嘴臉……十年!整整十年啊!
他祝汝昌,曾經也是鄉里寄予厚望的才子,曾經也對未來充滿了無限的嚮往!可如今呢?他成了一個人人可以踩上一腳的廢物,一個連妻兒都無法庇護的懦夫,一個全京城最大的笑話!
他的人生,就像這隻破碗,充滿了無法彌補的缺憾和裂痕!
他恨!恨紀曉嵐那個高高在上的老東西,躲在雲端之上,冷眼旁觀,看了他十年的笑話,想必心裡一定很得意吧!恨這個拜高踩低、世態炎涼的世界!更恨自己這身沒用的骨頭,怎麼就這麼不爭氣!
這一切的源頭是什麼?
就是那隻碗!那隻該死的破碗!是它,像一個詛咒,籠罩了他整整十年!是它,讓他背負了十年的枷鎖和恥辱!
對!就是它!
祝汝昌像是突然找到了所有痛苦的宣洩口,他跌跌撞撞地衝到屋角那個放碗的木架前,一把將那隻蒙著薄塵的破碗狠狠地抓在手裡。
這些年,他有過無數次想把它砸碎的衝動,但每一次,要麼被紀筠聲淚俱下地攔住,要麼就是被那句「不到山窮水盡」的鬼話所束縛。
今天,他覺得,自己已經死了。精神上,徹徹底底地死了。還有什麼,比現在更山窮水盡的?還有什麼,比眼睜睜看著女兒病重、全家即將流落街頭更絕望的?
沒有了!
他高高地舉起那隻碗,對著嚇得面無人色的紀筠,發出了狀若瘋狂的大笑,笑聲里充滿了悽厲和絕望。
「十年了!紀筠!你看到了嗎?整整十年了!我祝汝昌就是個天大的笑話!你爹送的這個『寶貝』,這個破碗,就是我祝汝昌的命!今天,我就親手把這條爛命給砸了!」
「什麼狗屁深意!什麼狗屁考驗!全都是騙人的!騙人的!!我再也不信了!!」
他歇斯底里地咆哮著,用盡全身的力氣,將碗高高地舉過了頭頂,手臂上的青筋虯結暴起,對準了腳下那片堅硬冰冷的青石板,狠狠地——砸了下去!
05
「不要——!」
紀筠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尖叫,她不顧一切地撲了過來,想要阻止丈夫這個瘋狂的舉動。裡屋的孩子們也被這恐怖的咆哮和母親的哭喊聲驚醒,發出了驚懼的大哭。
整個狹小而破敗的屋子裡,瞬間被絕望的氣息填滿。空氣仿佛凝固了,時間也似乎在這一刻被無限放慢。
祝汝昌的眼中,只剩下那片即將與碗碰撞的青石地面。他要砸碎它!砸碎這個折磨了他十年的噩夢!砸碎他這屈辱不堪的命運!
他的手腕已經開始發力,那隻破碗帶著風聲,以決絕的姿態向著地面墜落。
然而,就在他的手腕即將發力到極致、碗即將脫手而出的那一剎那,或許是由於情緒激動而手心出汗,又或許是剛才抓握得太過用力,他的大拇指,在碗底那個粗糙的、沒有上釉的圈足上,重重地、狠狠地滑了一下。
突然之間,祝汝他所有的動作,都僵在了那零點零一秒。那股毀天滅地般的滔天怒火,那份與世界同歸於盡的瘋狂決絕,仿佛被指尖傳來的一絲微不可察的異樣觸感,瞬間澆上了一盆冰水。
他的指尖,傳來一種極其奇怪的感覺。
不是普通陶土燒制後留下的那種粗糲、砂礫般的質感。而是在那一片粗糲之中,有一道極其細微、卻又異常清晰的凸起劃痕。它很短,很淺,若不刻意去摸,根本無法察覺。
但它又不同於燒窯時偶然留下的瑕疵,因為祝汝昌能清晰地感覺到,這道凸起有規律,有稜角,甚至……有筆鋒。
它像是……被人為刻上去的!
祝汝昌愣住了,像一尊石化的雕像,依舊保持著那個將碗砸向地面的姿勢,一動不動。他的大腦一片空白,所有的聲音——妻子的哀求,孩子的哭喊,窗外的風聲——全都在瞬間離他遠去。
這是什麼?
這個念頭像一顆石子,投進了他死寂的心湖。
十年了。整整十年,這隻碗就擺在他的家裡。他看過它無數次,也曾在盛怒之下摸過它幾次。可他從來沒有,也從來不屑於去仔細地觀察它的碗底。在他眼裡,這就是一件象徵著恥辱的垃圾。
偏偏在今天,在他最絕望、最痛苦、最瘋狂的時刻,在他下定決心要將它徹底毀滅的這一刻,這個隱藏了十年的秘密,才吝嗇地、悄悄地,向他展露了冰山一角。
這算什麼?是命運的又一次捉弄嗎?
祝汝昌慢慢地,幾乎是帶著一種神經質的顫抖,將高舉的胳T膊緩緩放了下來。
紀筠的哭聲戛然而止,她滿臉淚痕,不解地看著丈夫這奇怪的舉動。她以為他回心轉意了,連忙上前,想要去拿他手中的碗。
「別碰!」
祝汝昌低喝一聲,像是護著什麼稀世珍寶一樣,將碗緊緊地抱在了懷裡。
他沒有理會任何人,徑直走到那張破舊的方桌前,借著窗外滲透進來的、微弱的清冷月光,小心翼翼地將碗翻了過來,讓碗底朝上。
他低下頭,將眼睛湊了上去,近得幾乎要貼在碗底。
他屏住呼吸,伸出微微顫抖的食指,在那道神秘的、被污垢和歲月掩蓋的凸起上,反覆地、輕輕地摩挲著。
他的呼吸,一點一點地,變得急促起來。
那不是一道簡單的劃痕。
那是一個字。
一個用某種極其古老、他從未見過的篆體刻下的、小到幾乎無法用肉眼辨認的字……
06
祝汝昌像是著了魔。
他小心翼翼地捧著那隻碗,仿佛捧著的是一個剛剛降生的嬰兒。他讓紀筠打來一盆清水,然後親手、仔仔細細地,將那隻碗里里外外清洗了無數遍。他洗得極其認真,連碗口那處豁口的陳年茶漬都不放過,尤其是碗底的圈足,他用一塊軟布,蘸著水,一寸一寸地擦拭,生怕錯漏了任何細節。
紀筠站在一旁,看著丈夫這判若兩人的舉動,心中充滿了疑惑和一絲隱隱的期待。她看到丈夫的眼神,那是一種她已經有十年沒有見過的眼神——專注、探究、閃爍著一個讀書人獨有的、智慧的光芒。
當碗底圈足上最後一絲污垢被清水洗去,那個神秘的字,終於在微弱的油燈光下,顯露出了它的廬山真面目。
它非常小,刻工卻異常精湛。筆畫轉折之間,遒勁有力,充滿了古樸之意。
祝汝昌可以肯定,這絕不是一個常見的漢字。他飽讀詩書,經史子集無一不通,卻從未在任何典籍上見過這個字形。它更像是一種特殊的符號,一個專屬的印記。
一個「款」。
祝汝昌的腦中瞬間閃過這個詞。古代的瓷器,尤其是珍貴的官窯或私家窯口燒制的精品,往往會在器物底部留下特殊的款識,以作標記。
「筠兒,快,把我書箱裡那幾本講古玩雜項的書都拿來!」祝汝昌的聲音裡帶著一絲壓抑不住的激動。
紀筠立刻回過神來,手忙腳亂地把他那幾口破舊的書箱打開,將裡面那些紙頁泛黃、甚至有些殘破的藏書都抱了出來。
夫妻二人就在這盞昏黃的油燈下,把頭湊在一起,開始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探尋。祝汝昌一頁一頁地翻著書,紀筠則在一旁,舉著油燈,為他照亮。十年來的隔閡與冷漠,仿佛在這一刻悄然消融,他們又變回了當初那對心意相通、互相扶持的伴侶。
他們翻遍了《陶說》、《景德鎮陶錄》這些常見的書籍,一無所獲。祝汝昌並不氣餒,又從箱底翻出幾本市面上極為罕見的孤本殘卷。這些書,還是他當年進京時,從一個落魄老秀才手裡淘來的寶貝。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窗外的天色已經開始泛白。就在紀筠的眼皮開始打架,祝汝昌也快要放棄的時候,他的手指在一頁殘破的紙上停住了。
那是一本名為《古窯考》的殘卷,上面用蠅頭小楷記錄了許多早已湮沒在歷史長河中的古代窯口和款識。
祝汝昌的目光,死死地鎖定在了其中一段記載上。書上畫著一個與碗底那個字一模一樣的符號!
他的心「砰砰」地狂跳起來。
他指著那個字,聲音因為激動而微微發顫:「筠兒,你……你看!是它!就是它!」
紀筠也湊了過來,只見書上赫然寫著:
「前朝寧王,性好奢,於封地建私窯,延攬天下名匠,專燒秘瓷。其泥料甚奇,摻西域『流光石』粉末,燒成之器,迎光細察,可見五彩毫光流轉,肉眼幾不可辨,世稱『流光瓷』。瓷成,皆於器底足內,以精鋼之錐,刻『押』字暗款,其形如……」
後面的字跡已經模糊不清,但「押」字暗款這四個字,如同一道閃電,劈開了祝汝昌腦中的所有迷霧!
這個字,竟然是一個「押」!它不是產地,也不是工匠名,而是前朝一位權勢滔天的藩王——寧王府私家窯口的憑證!
祝汝昌立刻將碗舉起,對著從窗戶縫隙透進來的第一縷晨光,眯起眼睛仔細觀察。果然,他看到碗壁內側,隨著光線的轉動,有一層幾乎看不見的、如同彩虹般的淡淡光暈在緩緩流動!
若非事先知道,誰能發現這隻粗陋破碗上,竟藏著如此玄機!
可這又如何呢?即便這是價值連城的「流光瓷」,一隻破了口的碗,又能值幾個錢?難道紀曉嵐讓他等十年,就是為了讓他發現這是個古董?
祝汝昌的眉頭又皺了起來,他覺得事情沒那麼簡單。他強迫自己冷靜下來,繼續往下看那段殘存的文字。
在「押」字款的圖樣下面,還有一行模糊的小字,像是後人加上的註解:
「……寧王事敗,家財散盡,其後人輾轉流落。聞寧王曾於京中設一錢莊為退路,後易名為『德昌記』當鋪,世代相傳。凡持『押』字款信物者,皆可至此……」
後面的文字,被蟲蛀掉了一個大洞。
但「德昌記」當鋪這四個字,清晰無比!
祝汝昌和紀筠對視一眼,都在對方的眼中看到了震驚和不敢置信。
德昌記當鋪!那不是就在他們家往東兩條街外,那家門面小得毫不起眼,看起來總是半死不活的當鋪嗎?祝汝昌曾無數次路過那裡,甚至有幾次窘迫到了極點,想進去當掉身上最後一件值錢的東西,但都因為那家店看起來生意太冷清,怕當不了幾個錢而作罷。
一個瘋狂的念頭,在祝汝昌的腦海中形成。
這隻碗,不僅僅是一隻碗。
它是一把鑰匙!一把開啟某個巨大秘密的鑰匙!
07
天一亮,祝汝昌就再也坐不住了。
他將那隻碗用布里三層外三層地包好,小心翼翼地揣進懷裡,那神情,比當年赴京趕考時揣著自己的得意文章還要鄭重。
「夫君,我跟你一起去。」紀筠不放心,堅持要陪著他。
祝汝昌看著妻子擔憂的眼神,點了點頭。他牽起紀筠的手,十年了,他第一次如此用力地、堅定地握著她的手。
夫妻二人懷著一種近乎朝聖般的忐忑心情,來到了那家「德昌記」當鋪門前。
這家當鋪的門面確實太小了,夾在兩家熱鬧的雜貨鋪中間,不仔細看根本發現不了。一塊褪了色的「德昌記」牌匾歪歪斜斜地掛著,門前的櫃檯積了一層薄灰,櫃檯後面,一個頭髮花白、看起來隨時都能睡過去的老頭,正有一下沒一下地打著算盤。
看到祝汝昌和紀筠進來,那老師傅連眼皮都沒抬一下,懶洋洋地問:「當東西?」
祝汝昌深吸一口氣,走上前,並沒有拿出懷裡的碗,而是壓低聲音,試探性地問:「老師傅,晚生想請教一下,您這裡……可認得一種『押』字款的信物?」
他話音剛落,那原本昏昏欲睡的老師傅,渾身猛地一震。他那雙渾濁的老眼瞬間睜開,射出一道精光,上上下下地將祝汝昌打量了一遍,又看了看他身邊的紀筠。
「東西帶來了嗎?」老師傅的聲音變得沉穩而嚴肅。
祝汝昌心中一凜,知道自己找對地方了。他從懷中,小心翼翼地取出那只用布包著的破碗,放在了櫃檯上,然後將碗底翻了過來,露出了那個清晰的「押」字。
老師傅的眼睛瞬間亮了。他戴上一副老花鏡,從抽屜里取出一個類似放大鏡的奇特工具,對著那個「押」字,仔仔細細地勘驗了半晌。他又用指甲在碗壁上輕輕颳了一下,湊到光線下反覆察看。
半晌,他放下工具,長長地舒了一口氣,臉上露出了如釋重負的表情。
他對著祝汝昌和紀筠,恭恭敬敬地躬身一揖:「二位貴客,小老兒……等了你們十年了!」
說完,他不再多言,繞出櫃檯,將二人請進了當鋪的內堂。
內堂陳設簡單,卻打掃得一塵不染。老師傅關上門,從牆角一個不起眼的暗格里,吃力地拖出一個巨大的、上了銅鎖的樟木箱子。
「祝相公,紀小姐,」老師傅擦了擦額頭的汗,語氣里充滿了敬意,「十年前,紀大學士親自來到這裡,存下了這個箱子,並留下了這隻碗作為信物。大人當時交代,這箱子裡的東西,是給二姑爺和二小姐的。但是,有一個規矩。」
祝汝昌屏息凝神地聽著。
「大人說,只有當他的女婿,祝相公您,親自、並且是獨立地發現了這碗底的秘密,悟到了其中的玄機,才能來取。若是紀小姐您,或者紀府的其他人拿著這隻碗來,小老兒一概不認。」
「大人還說,」老師傅看了一眼祝汝昌,眼神複雜,「若是這隻碗,在中途被打碎了,那麼這個箱子,將由小老兒親手焚毀,永遠封存。」
祝汝昌聽到這裡,只覺得背後一陣冷汗。他想起了昨夜,那隻碗離地面只有咫尺之遙,只要他再多用一分力,只要他的手指沒有那一下鬼使神差的滑動,這箱子裡的一切,就將與他永遠失之交臂。
老師傅用一把古舊的鑰匙,打開了銅鎖,「咔噠」一聲,在寂靜的內堂里顯得格外清脆。
他掀開了沉重的箱蓋。
箱子裡面,沒有祝汝昌想像中的金銀珠寶,黃白之物。
最上面一層,是厚厚的一疊地契和房契。祝汝昌顫抖著手拿起來一看,上面赫然寫著:京郊良田三百畝,城中臨街旺鋪三間!
這……這才是真正的嫁妝!
紀筠也捂住了嘴,眼中滿是淚水。
祝汝昌接著往下看,箱子的中層,整整齊齊地碼放著數百冊書籍。他只抽出一本來看,便呼吸一滯。那是一本宋版的《資治通鑑》殘卷,是市面上早已絕版的孤本!他再翻看其他的書,無一不是價值連城的古籍善本。對於一個真正的讀書人來說,這比金山銀山還要寶貴!
而在箱子的最底層,靜靜地躺著一張摺疊的素箋。它沒有用信封封口,更像是一張隨手寫下的留言條。
祝汝昌拿起那張素箋,展開。
上面,是紀曉嵐那熟悉而蒼勁的筆跡,只有短短兩行字:
器毀則才亡,人窮則志堅。
十年磨一劍,今朝始出鞘。
短短十六個字,像十六記重錘,狠狠地敲在了祝汝昌的心上。
在這一瞬間,所有的屈辱,所有的不甘,所有的怨恨,都化為了醍醐灌頂般的徹骨明悟!
他終於明白了!他全明白了!
岳父紀曉嵐,根本不是在羞辱他,也不是在看他的笑話。他是在用一種最極端、最殘酷的方式,磨練他的心性!
如果十年前,岳父直接把這些財富交給他,以他當時年少得志、心高氣傲的心態,極有可能會被這突如其來的富貴迷了心竅,從此耽於享樂,荒廢了學業和銳氣。
所以,岳父給了他一隻破碗,給了他一個「破碗女婿」的惡名,讓他從雲端跌入泥淖,讓他嘗盡人間冷暖、世態炎涼。他要磨掉他身上的浮躁之氣,要鍛鍊他處變不驚的韌性,要看看他在這真正的「山窮水盡」之中,是否還能保持一個讀書人的風骨、一個逆境求生者的觀察力,去發現那個近在眼前、卻又被所有人忽視的秘密!
「器毀則才亡」,如果他連這點挫折都承受不住,心灰意冷,甚至遷怒於物,將碗砸碎,那就證明他心智脆弱,不堪大用,才華也終將因此而毀滅。
「人窮則志堅」,只有經歷過真正的貧窮和絕望,才能真正懂得民生疾苦,才能磨練出堅不可摧的意志。
這隻破碗,既是十年殘酷的考驗,也是一道最嚴密的保護。它保護了他的初心,砥礪了他的心志。這十年的白眼,十年的屈辱,這十年所有的苦難,原來,才是岳父贈予他的一生中最寶貴、最厚重的一筆財富!
祝汝昌手捧著那些地契和書冊,看著那兩行字,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他這個七尺男兒,「噗通」一聲跪倒在地,朝著紀府的方向,泣不成聲,重重地、一個接一個地,磕了三個響頭。
這一拜,是悔恨。
這一拜,是感激。
這一拜,是新生。
08
有了田產和商鋪的穩定收入,祝汝昌一家的生活,幾乎是一夜之間,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那些田地和鋪子,早就由紀府的忠僕代為打理得井井有條,每年都有極為可觀的進項。
他再也不需要為了下一頓飯而發愁,再也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臉色。
但他沒有像那些一夜暴富的庸人一樣,立刻搬進豪宅,買奴僕,穿錦衣。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揣著銀子,去城裡最好的藥鋪,為女兒請了最好的大夫,抓了最好的藥。看著女兒的病一天天好起來,重新恢復了活潑,他覺得比自己中了狀元還要高興。
第二件事,他用一筆錢,把他住了十年的那間破敗小院給買了下來。紀筠不解,問他為何不換個大宅子。祝汝昌只是笑了笑,說:「這裡,是我們真正的家。我不想忘了我們是從哪裡走出來的。」
他把院子重新修葺了一番,尤其那間小小的書房,他換上了寬大的書案和明亮的窗戶,然後將那幾百冊從「德昌記」取回的孤本古籍,一本本地、視若珍寶地擺上了新做的書架。
整個人,從裡到外,都變了。
他不再是那個敏感自卑、眼神麻木的中年人,也不再是那個憤世嫉俗、動輒發怒的酒鬼。他腰杆重新挺直了,眼神也重新變得清亮、沉穩、溫和。那十年歲月刻下的風霜,仿佛一夜之間被撫平,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經歷過大起大落後的淡定與從容。
他待人接物,平和謙遜。那些曾經嘲笑過他、鄙夷過他的街坊鄰里,見到他如今的變化和富裕,一個個都換上了恭敬諂媚的笑臉,變著法兒地來巴結討好。祝汝昌並不在意,也從不報復,只是淡淡一笑,與他們保持著不遠不近的距離。
心無旁騖之後,祝汝昌將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學問之中。他白日裡研讀那些珍貴的古籍,夜晚則靜坐思考。十年的底層生活,讓他對民生疾苦有了最深刻的洞察。他的文章,褪去了年少時的華而不實,變得老辣而深刻,字裡行間充滿了對現實的關懷和悲憫。
又過了三年,朝廷再開恩科。祝汝昌平靜地走進了曾經讓他三次折戟的貢院。
這一次,他下筆從容,一氣呵成。放榜之日,他的名字赫然在列,高中二甲進士。雖然不是狀元,但這個成績,足以讓他踏入仕途,實現自己真正的抱負。主考官在批閱他的策論時,曾大加讚賞,稱其「言之有物,字字泣血,非經歷世事者不能為此文」。
故事的結尾,是幾年後的一個冬日。紀曉嵐七十大壽,紀府高朋滿座,熱鬧非凡。
祝汝昌身著一身得體的官服,氣度不凡,早已不是當年那個窘迫的寒門書生。他牽著溫婉賢淑的紀筠,帶著一雙活潑可愛的兒女,回到了紀府,為岳父祝壽。
席間,他沒有提當年任何事,也沒有說任何感激的話。只是在壽宴開始前,親手為岳父紀曉嵐奉上了一杯新茶。
紀曉嵐端坐在太師椅上,看著眼前這個氣度沉穩、眼神堅毅的女婿,接過茶杯,輕輕抿了一口。他渾濁而睿智的眼中,閃過一絲滿意的笑意,捋著花白的鬍鬚,點了點頭。
翁婿二人相視一笑,一切盡在不言中。
 呂純弘 • 116K次觀看
呂純弘 • 116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19K次觀看
呂純弘 • 19K次觀看 花峰婉 • 17K次觀看
花峰婉 • 17K次觀看 呂純弘 • 10K次觀看
呂純弘 • 10K次觀看 花峰婉 • 6K次觀看
花峰婉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9K次觀看
呂純弘 • 9K次觀看 奚芝厚 • 8K次觀看
奚芝厚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7K次觀看
呂純弘 • 7K次觀看 呂純弘 • 23K次觀看
呂純弘 • 23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滿素荷 • 4K次觀看
滿素荷 • 4K次觀看 喬峰傳 • 34K次觀看
喬峰傳 • 34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23K次觀看
呂純弘 • 23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9K次觀看
呂純弘 • 49K次觀看 幸山輪 • 22K次觀看
幸山輪 • 22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